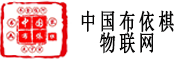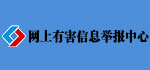本文以《红楼梦》为对象,结合书中女性生活的公共区域与私人空间,综合探讨琴棋书画相关概念和中国清代才女观的表现方式,以及书中不同于世俗文本琴棋书画的普遍描绘方式。
旨在从性别学视域探究书中“琴棋书画”所反映的拟男之风与风雅所附,及其在生活空间、文人交游、社会层次、女性角色影响下的社会意义与时代局限。
一、琴棋书画绪论
在传统文人领域的音乐活动中,琴渐渐具有了超出乐器本身的文化蕴涵。弹琴,不仅仅是技能的体现,更是托物言志的体现。琴的核心部分当属对恬淡冲和境界的向往,对知音的渴望,对人格的坚守,这较多通过士人的诗文表现出来。
书法是中国艺术和文化的中心和基础,也是中国最为广泛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古代的大部分人会书写,尤其是士大夫阶层。
书写,是中国古代文人仕途必须借由的途径,从实用的书写中产生,又逐渐成为艺术。书法既包括字体,也涉及风格,其发展具有连贯性,东晋时期形成的一些经典风格,此后数千年仍被摹写。
另一类为读书,读书为古代文人取仕必经之途,而对宦官家族女性或其他以才情著称的女性来言,读写诗书则是个人修养的提升。结合文本和图像,明清女性的琴棋书画中的书更多偏向于对诗书的阅读。
在画的方面,传统绘画种类繁多,有宗教画、水墨画等各种类别;从其发展来看,早期以功用性为主,既包括为宗教服务,也包括为宫所用;内容以记录、宣传等为主,画家的个人情感流露不多。
宋代以来,中国文人画兴起,清时期成为文人寄情于景的表达方式。
在艺术家追求画笔自由的同时,一些兰竹山石等绘画母题也随画谱传播,绘画得以更为广泛地普及。明清文人墨客赏画作画,闺房女性中也多有赏画之风,并有少数画作传世。
二、琴棋书画和女性二重空间
琴棋书画在明清小说中常用于对女性的描述,相较于其他文本而言,《红楼梦》的琴棋书画不局限于简单的才能描述,还在作者的情节描述中具有一定的叙事性功能。
在《红楼梦》大观园这相对独立的女性空间中,琴棋书画与女性为主的人物主体研修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从庭院和闺房等不同角度展示了女性在二重空间与琴棋书画的关联。
晚明江南一带园林盛行,这些场所大部分与男性的退隐或在职的文人官员紧密相关,呈现出一个个私人控制的社会空间,也是园林主人避开公众压力、行使道德权威的场所。
至清代,晚明的园林被陆续易主,新的皇家或私人园林也在不断地兴建。
相较于这些园林,《红楼梦》大观园体现了不同的女性视角,不仅是其兴建源于贾元春,园林的命名等也是由林黛玉等贾府女性参与,并最终由贾元春、贾府中与皇权相连、地位崇高的女性来确定完成,甚至亲笔题名。
大观园建筑也在这一书法净化过程后,最终确立为女性世界。《红楼梦》多次论及清代仕女生活的各方面,并随着特定人物的代入,反映出“闺阁中历历有人”及“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等主旨。
这样的一个女性世界也成为一个相对于外界而独立存在的女性空间,即被认知、想象、表现为女性的真实或虚构的场所。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人所绘《大观园》为例,画卷纵137厘米,横362厘米,绘画了大观园内的百余名女性群体。
其所处的画面背景建筑中既包括凹晶馆、凸碧山庄等女性在庭院中吟诗、赏月等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也有蘅芜院、寥风轩即以薛宝钗和贾惜春为代表的女性闺房私人空间。
棋琴书画在《红楼梦》中也有所提及,书中棋指围棋,除了明言的“围棋”“大棋”外,其他如下棋、着棋等也指围棋。金陵十二钗为主的年轻仕女们多谙习围棋之道。
书中共有18处提及下棋,除贾政、宝玉外,大多表现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惜春等闺阁女性日常闲暇,书中第四章回《薄命郎偏逢薄命女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提到“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姐妹等一处,或看书下棋,或做针线,倒也十分相安。”
这与同一章回提到的贾府男性代表人物贾政“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的文人日常闲暇生活极为相近。此外,对弈也体现了书中仕女们与宝玉的交流。
书中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宝玉每日只和姊妹丫餐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书中也提及“设色琐论对各类颜料均有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红楼梦》里的仕女中,惜春擅绘画,但此处薛宝钗的详细答疑,则表明薛宝钗等其他园中仕女也通晓绘画,并备有相应画材。有意思的是,惜春的大观园全图在书中并没有完成。
薛宝钗也指出其中的难点,因为大观园似画,但在绘画中如要真实反映,则需用“界画”的专业方式,这一术语也可译作“格线幽”,是宋兀十三科之一,或以大观园外男性复制原来画工描绘的建筑图样,再加上人物。
但业余的贾惜春,并不能熟练掌握这些专业透视技法,也很难以脱离所在女性空间外的视角客观描绘惜春的绘画才能,更趋于男性文人业余的写意绘画,以陶冶性情为主,而非追求画工之能。
这种绘画活动也存在于书中薛宝钗等其他仕女们常生活之中。清代江南是女性文学的核心地区,精英阶层的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红楼梦》中的女性大多读得诗书,女性的吟诗赋词文中也多有描述。
元妃省亲章节中,曾命园中姐妹各赋五言律一首。庭院仕女还专门创立诗社,结社雅集。
清代女性结社有多种形式,如家门血缘型、地域型、师门型和社交型等,其中早期女性诗社多为家族血缘型,带有明显的家庭化倾向,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也是如此。
文中提及探春曾邀请姐妹们创立诗社,结社文中便有“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山东之雅会,让余脂粉”等。
三、拟男之风与风雅所附
“拟男”一词,早期多见于戏曲研究,指女作者将自我剧作化,成为剧中主角时,保留女性身份,却以男子外形出现,由生角主演,用男子身份来抒情与叙事的表现形式。
“拟男”这一文化现象,体现出明清时期女性意识已经觉醒。她们不愿意被圈定在封建社会规定的角色中,而要描绘真实的“自我形象”,是女性对封建礼教突破性的叛逆与挑战,意义极其深远。
哪男在《红楼梦》女性形象的表达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王熙凤。《红楼梦》的女性人数众多,但在其中作为权力的主导方,主要是由在贾府中年龄居长的贾母表现,而王熙凤是其中具有权力的年轻女性代表。
在书中的人物刻画中,既有对其权力的运筹帷幄,也有具体化的男子气概。
嘴时,《红楼梦》中女性人物的名字也有拟男之处,书中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在介绍人物名称时,贾雨村曾道,“甄家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并以此为雅,反之为俗。
即便是王熙凤的姓名,也在书中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中提到戏文《凤求鸾》中的公子与之重名。也正是在这样通俗戏文中,才将琴棋书画描写为女子才能:“小姐芳名叫作雏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这也是明清时期社会常见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对于女性才能最常见的描绘方式,但在《红楼梦》中,类似的描写仅出现此处,且文中连贾母亦觉俗套。
《红楼梦》对于主要仕女的描述中,琴棋书画并非仅停留在这样的一种世俗表象,而是交叉描写,以融入性的文笔展开,结合仕女庭院闺房等多重生活空间,突出其与男性文人风雅的共性。
特别是在江南带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这一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已从传统的闺门,拓展到结社雅集、书画创作等各方面。
参照男子的蒙学教育形式,不同层次的女性经私学“义学”“乡学”等方式,都得以接触诗书文字,也即“女学”开展的启蒙阶段。
传统的“琴棋书画、吟诗赋词”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生活的主要部分,而在清代仕女日常生活中也渐成主流。《红楼梦》文本中仕女们对琴棋书画的日常研习也是“拟男”时风的反映,更接近文人儒士对琴棋书画的赏学之态。
女性的琴棋书画在书中除了在上述仕女的生活空间中阐述外,同时还在不同社会层次、不同年龄的女性中,以才能、姓名、叙事情节转承等多方面加以描绘。不同女性对琴棋画的表达既有偏重,又不乏交融相会。
复调是18世纪之前在欧洲巴洛克中盛行的一种形式。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具有相对独立的旋律线,有机结合,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
《红楼梦》中女性形象塑造正具有多重性复调表达方式,女性在情节叙事中的主体性较其他同期作品都更为突出。
总结
明清女性的琴棋书画来对男性文人群体附庸雅的时多是指抚琴弈读书、吟诗、书写绘画等综合文艺修养。既有男性文人的推崇,也有女性彼此间的交游影响。
从明代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对女性“琴棋书画”的概括性描述,到清代《红楼梦》文学中与主要描述对象在叙事性、命名、才能、社会功能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表达,体现了性别学视野下明清女性群体的生活空间和个人情感才能。
除文本外,明清时期的绘画和瓷器等艺术品中,也同样体现了女性琴棋书画主题,特别是在明清瓷器装饰中,还出现了“琴棋书画”结合的装饰主题,反映时风。
从书中描述的不同层次女性来看,“琴棋书画”主要与未出阁的闺秀群体相联,但这些才能并非是对琴棋书画中某一门类技能的追求,而是跟随男性文人群体的抚琴对弈,吟诗赋词,写意绘画的特质,以不同闺秀等人物间的交流,及所处的公共或私人二重空间,反映彼此在琴棋书画的综合修养。
但在时代的局限性中,这些琴棋书画的拟男之风最终沉寂于清代女性的妇人日常模式和家庭教育功能。